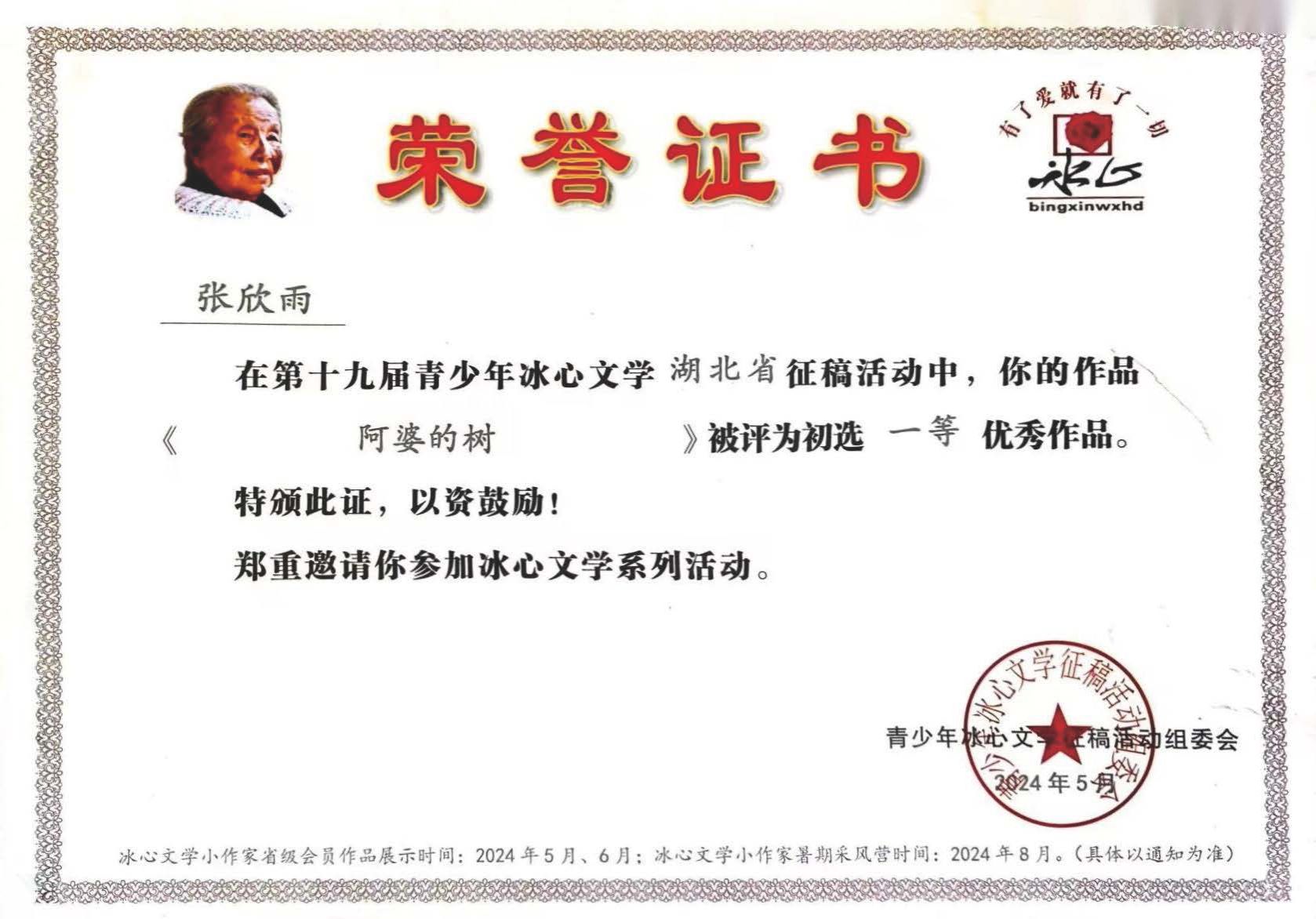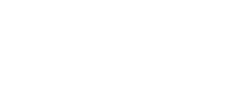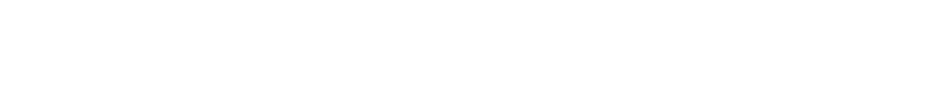砰,一群麻雀腾空而起,大树轰然倒下,就像老屋被钉上的门窗,再无声响。我摩挲深褐色的树干,凹凸不平,仿佛老人爬满了皱纹的苍老的脸,又像是老人青筋暴起、骨瘦如柴,却又布满了老茧的饱经沧桑的手。很快,就被政府的车拉走了,只剩下满院的狼藉。母亲喃喃道说阿婆的最后一丝念想也随着她走了,她的眼里盛着轻光,如黑夜中的月光一般轻绵柔软,却沉沉地散着不知所以的愁。
阿婆的院子只栽了一棵树,如她一般深深的扎入地下。
阿婆的树在我出生时便已那般高了,横在小院斑驳的墙前。儿时记忆中,阿婆便时时凝望着,无声无响,不知道在想着什么。眸光烁烁,印照着树,从叶脉到根茎,无一处遗漏。幼时的我总是问她这大树有啥好看的,不如万丈光辉的街道上各式各样的糖果。她扬起嘴角,用粗糙的手抚摸树干,仿若与树皮合为一体。听见她轻一笑,用干瘪的脚撑起自己长吐一口浊气:“人总要有根呐。”我笑她糊涂了,人是人,树是树,人怎么会有根呢?她却从来不答。
阿婆的树下摆着摇椅,掘说是很老旧的了,吱嘎吱嘎地响,夏天很热地,很沉地伏在树上。只漏下些许,洒在她身上。阿婆的故事断断续续,拼拼凑凑,缭绕着乡音,伏在叶脉上,散着夏日的炎热。提起阿公,她总欣喜着张望起那颗大树,眼睛微眯着映着阳光,椅子便嘎吱嘎吱的响起来。她向来爱讲小院的故事,一草一木,一砖一瓦,与阿公一点一点布置,那颗大树也是阿公亲手种下的。那时她说着说着总抚着我的头,又望向小院,眼里无限柔情。她说那就是根,就是家。
可惜幼时顽劣并不懂得,没听两句就奔出小院。那时,我很爱携同伙伴在起伏屋影下疾奔,追逐受惊的落日。我们贴着冰滑的玻璃,扶着木质窗框,玩具店中布谷鸟跃动在黑漆木门内。街灯在繁星漫出黑云时准时亮起,浅色的光影在叶隙中流动,琉璃般的灯火泛动光辉,使常居一角的我得到满足。那时的我,总觉得还有几年几日,把阿婆一人丢在家里,独享一个孤独的晚年。现在想想,我可真是太聪明了。
阿婆一生清苦,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,幸得遇上了阿公,待她如挚爱,百般呵护。不幸的是阿公因病早早离世,留下年幼的母亲,阿婆只好咽下生活带给她的破碎和苦楚。在那样一个年代,一个女人孤身一人带着孩子,又不肯再嫁,日子是何等的艰辛。省吃俭用,将女儿送出了小山村,自己却从未见过外面的世界 。女儿出息后,多次与阿婆商量让她搬出来住,阿婆却总是执意要守着她的小院和树,说走了阿公就没办法回家了。
叶上的岁月流转匆忙,未想再次见面便是诀别。那树好像又长了,但终是看不见了。高高的枝插进高高的云,停了,停了;深深的根钻向深深的壤,长着,长着。我跨进屋内,门槛记得是要跳过去的,但现在跨进跨出又变得很容易随性了。
一别数月,小院如初,不想故人不在,如今连那颗大树也不在了,本来想着护住这棵树也算是护住最后的点念想,没成想道路建设需要征收,再求情也是没办法的。母亲说起阿婆临走前还唤着把窗子打开些,盯见那棵很老很老的树。她望向那,眷恋的,像是确定着什么。然后就再没有声息,像一个匆匆打下的句点。
望向那树桩,光秃秃的,在我眼里似乎越来越远,我不禁想到,此后我与她之间的距离就遥远起来,像树冠延到天上了,再也瞧不见。
母亲缓缓说到:“人是有根的,就像这树一样,树冠再高,根不着地,也是无益。”她缓缓摸向那截面,就像阿婆当年亲切地抚摸着树干。对啊,人总是有根的,根在,人就在。